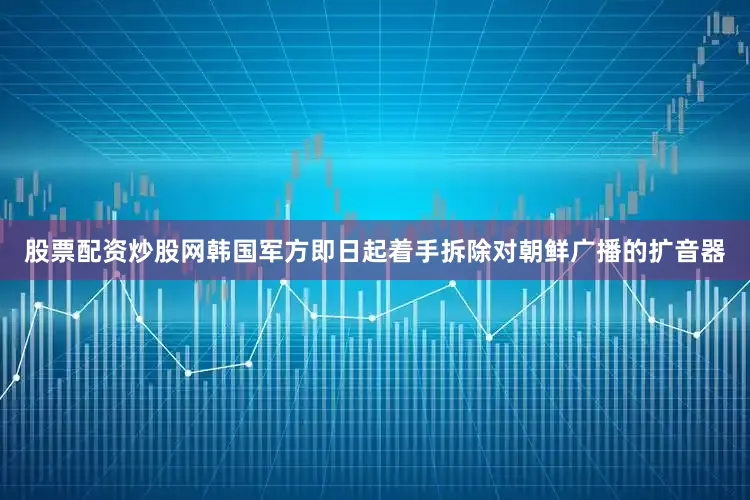2025年西城区图书馆“西城,不能忘却的纪念”征文选27
青灯下的独行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的七年
文/秦旭东
1925年鲁迅摄于北京
我住在西城区牛街,离绍兴会馆不过几步路。晚饭后散步,总习惯绕到南半截胡同,在那座灰砖小院前站一会儿。红色的院门常闭着,门口北侧的灰砖墙上还“顽强”地悬挂者1990年12月(老)宣武区人民政府公布、(老)宣武区文化文物局1991年3月立的白色石牌,上书“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绍兴会馆”。会馆左侧地上立一石碑,碑上文字为“2011年6月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会馆墙角地面爬着几株野草,默默叙述着这里曾经的往事。一百多年前,那个叫周树人的绍兴人,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沉默也最激烈的七年半时间。这,也是鲁迅“北漂”十四年的起点。
展开剩余85%绍兴会馆灰墙上的牌子
1912年5月的北京,鲁迅随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北迁,住进了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里。会馆坐西朝东,南中北三路院落,大小房屋84间。鲁迅起初住在会馆里的藤花别馆,这藤花馆名字好听,但环境很差。鲁迅住进第一个晚上,就被三四十只臭虫骚扰,不得不转移到桌上去睡,加上人声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见《鲁迅日记》)。忍耐了四年后,他搬到会馆相对安静的补树书屋。为什么叫补树书屋呢?据说院中原来有一棵大楝树,被大风刮倒,又补种了一棵槐树,所以叫补树书屋。屋子不大,窗前这棵补种的槐树也长大了。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街坊们都说这屋子不吉利,鲁迅却不在意,在日记里写下“聊避风雨,且省房租”。他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就伏在那张旧书桌上抄古碑。阴森森的小屋里,一盏煤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我常想,那时的南半截胡同该是什么样子?没有现在这些汽车喇叭声手机铃声,只有更夫打梆子的声音在夜色里回荡。鲁迅就坐在窗前,听着外面的更声,一笔一画地抄着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碑文。他后来在文章里说,那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可我知道,他哪里是在麻醉自己,分明是在积蓄力量。
前两天我带着女儿悠悠和她的闺蜜可心再次来到绍兴会馆。她们今年小升初,她闺蜜9月就要到鲁迅中学去读书,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前来绍兴会馆实地了解一下鲁迅当年的住处和创作的经历。可近期会馆院子大门紧锁,我只好站在门口大概讲了讲。我之前多次进来过,了解到这里是一处大杂院,住了很多户居民,现在已全部腾退。有个住在附近的老人告诉我,他爷爷那会儿见过鲁迅,说是个“瘦瘦的,不爱说话,走路特别快”。我想象着他夹着公文包匆匆穿过胡同的样子,和现在下班回家的上班族也没什么两样吧。老人说,今后这里将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会馆分馆,继续讲述历史,传承文化。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让我感慨的是,在会馆简陋的补树书屋里,1918年4月,鲁迅创作出第一篇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我想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那天夜里,胡同里一定很安静,只有毛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写到这里时,手,会不会发抖?心,会不会颤抖?
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
周树人为什么去创作这篇小说呢?
在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第13集里,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四人结伴前往北京绍兴会馆,在朴树书屋拜访周树人。周树人在交谈中强调,推广白话文的最佳方式是创作白话小说。陈独秀的高度认可这一观点,当场邀请周树人为《新青年》撰写白话小说。深受身边亲友被封建礼教迫害的触动,周树人在绍兴会馆构思酝酿,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在艺术表现上,塑造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狂人”形象,通过其错乱癫狂的内心独白,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作者刻意采用语序颠倒、逻辑混乱的叙述方式,精准再现了精神病患者的思维特征。从思想内涵来看,作品展现了双重批判维度:一方面是对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无情鞭挞,另一方面则流露出创作者深沉的自我反省意识。鲁迅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不仅批判了传统文化的积弊,更表达了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篇末“救救孩子”呐喊,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声,既体现了作者对未来的期许,也暗示了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性。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部作品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不仅是鲁迅个人创作生涯中的首部白话小说,更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学创作走向成熟。其问世彻底打破了文言写作的传统范式,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树立了典范,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再次去往鲁迅的故乡绍兴,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有关鲁迅的文献资料。
据记载,鲁迅在绍兴会馆的饮食颇为简单,但因家乡情结,仍保留了不少绍兴习惯。
鲁迅极爱茴香豆。据其日记记载,1912年12月某日,“午后至青云阁啜茗,购茴香豆一包,费铜元七枚”。他偶尔也喝点黄酒,但因囊中羞涩,很少豪饮。晚餐多吃面食与鱼虾,若有余钱,他会去附近的“广和居”叫一碗虾仁面或炒鳝丝,但次数很少。大多手头紧,就在会馆煮挂面,拌点酱油、猪油,撒些葱花,谓之“阳春面”。夜宵多吃烤白薯与炒花生。日记里说,冬夜写作时,他常让门房小栓去街边买烤白薯,或自己用炭炉炒一捧花生,边剥边写。
二弟周作人后来回忆:“大哥(鲁迅)尤爱咸齑(腌菜),每晨必啜粥两碗,谓可醒脑。”他常在会馆附近的早点摊买粥,佐以自备的绍兴梅干菜或酱萝卜。
我踟蹰徘徊在北京绍兴会馆门口,总觉得下一秒就会有个穿着一袭长衫、留着硬发平头的人推门出来,若真如此,我定带他看看今天的北京、今天的西城……
七年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鲁迅在这里抄了六千多张古碑,写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还有《阿Q正传》的开头。后来他搬去了八道湾,再后来离开了北京。但我觉得,他生命中最重要转变,就是在北京西城这座小院里完成的。
人虽走了,但文魄却留在了南半截胡同的青砖灰瓦里。
如今,我站在会馆门口,看着三三两两的人群,感慨万千。一百多年过去了,胡同变了很多,但有些东西似乎没变。那个在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那些穿透时间的文字,还有我们这些后来者,依然在试图理解鲁迅当年的愤怒与孤独。
透过宣南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南半截胡同,我的目光始终盯着绍兴会馆这块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地,任由思绪随风飘散。悠悠在此,可心已远……
【作者简介】
秦旭东,西城区牛街居民,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证券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河南思客》等。
西城
信息咨询组
发布于:北京市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掘金配资,恒信宝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炒股配资网立足长清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 下一篇:现货配资平台这样的日子很适合出游